
很多翻译过来的书都带着一股洋腔调,并且有的修辞出现明显的问题,很多罗列在一起的翻译词语综合运用,注意保持了原来语言的句式,却忽略了汉语的句式和修辞,结果往往成了诘屈聱牙的东西。那么,翻译的误译也就显露出来。

鲁迅在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一文中写道:“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,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,译完一看,晦涩,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;倘将仂句拆下来呢,又失了原来的语气。在我,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,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,所余的惟一的希望,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。”而这“硬着头皮看下去”不过是一种谦虚的说法,却恰恰给了批评者梁实秋以口实。梁实秋在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一文中引用陈西滢的论述:“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,可是流弊比较的少,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,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。”还说“我私人的意思总以为译书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令人看得懂,译出来而令人看不懂,那不是白费读者的时力么?曲译诚然要不得,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,把精华译成了糟粕,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,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,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,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,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,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,而你读的时候竟还落个爽快。”其实是在批评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,但鲁迅先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说“我的译作,本不在博读者的‘爽快’,却往往给以不舒服,甚而至于使人气闷,憎恶,愤恨。读了会‘落个爽快’的东西,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:徐志摩先生的诗,沈从文,凌叔华先生的小说,陈西滢(即陈源)先生的闲话,梁实秋先生的批评,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,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。”说了一大堆,对他们的文章并没有什么好感。
翻译当然不能硬译,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来翻译,还要结合外文的语法句法文法来翻译。鲁迅论述道“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,较易于翻译外国文,语系相近的,也较易于翻译,而且也是一种工作。荷兰翻德国,俄国翻波兰,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?日本语和欧美很‘不同’,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,比起古文来,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,开初自然是须‘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’,很给了一些人不‘愉快’的,但经找寻和习惯,现在已经同化,成为己有了。中国的文法,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,然而也曾有些变迁,例如《史》《汉》不同于《书经》,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《史》《汉》;有添造,例如唐译佛经,元译上谕,当时很有些“文法句法词法”是生造的,一经习用,便不必伸出手指,就懂得了。现在又来了‘外国文’,许多句子,即也须新造,——说得坏点,就是硬造。据我的经验,这样译来,较之化为几句,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,但因为有待于新造,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。”中国的语言有别于外文,尤其是翻译一些古典哲学和文学著作,一般都会出现很多的误译现象。硬译不可靠,让人读者爽快的翻译更不可靠。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,提倡信、达、雅,有很多硬译的成分,也有很多率性而为的东西,都成了误译,但在当时的环境氛围中,并不影响传播。林纾翻译的小说大多都是听别人口译过来的,只是了解故事梗概,就匆匆整理成文言文,发表出去,尤其翻译的《茶花女遗事》一炮走红,一时间洛阳纸贵,名声大噪。其实,他只顾及了达与雅,却在信的方面没有深究。此后,虽然林纾与海外才子们合作,翻译了180余部小说,但总体上是一个水平,并不能成为经典的译本,只能成为他二度创作的译本,甚至有他随意想象的成分在里面,也就不能绝对忠实于原著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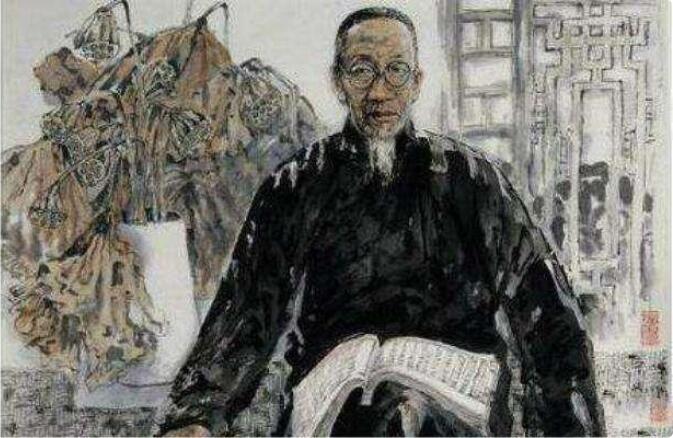
误译造成了误读,很多人一味盲目信任翻译人的水平,结果在读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不合情理之处,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,只能借助注释来读,却中了误译的毒。而且时代不同,读不同时代的翻译著作竟然发现很多笑料。以前人们翻译的东西和现在人们翻译的东西竟然大相径庭。试读林纾的《茶花女遗事》和现在人们翻译的《茶花女》,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。再看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的翻译,仅仅玄奘一个人的翻译就流传了上千年,而在这上千年的时间里,各种读法层出不穷,因为当时翻译的译文是没有标点的,只能由后人来加标点,标点不同,句意也就不同,但原著究竟如何,还得靠懂梵文的学者去深究,看看当年玄奘翻译的时候有没有“硬译”或“图了爽快”,有没有“夹带私货”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现在的老百姓不仅绝不可能去读玄奘和鸠摩罗什,甚至读孔孟、老庄也得慎思而行,毕竟,古今汉语间也存在着转渡的问题。于是,严复、贺麟、朱光潜等人的翻译就成了罪不抵功的翻译,与其误译,不如不译,以免造成谬种流传的问题。或许,这是一种认真而决绝的态度。
看看外国人是如何翻译的,海德格尔翻译过老子的《道德经》,布伯翻译过庄子的《南华经》,叔本华翻译过印度的《奥义书》,伯格森翻译过《卢克莱修文集》,同代的利科翻译过胡塞尔的《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》第一卷和《第一哲学》,莱维纳翻译过胡塞尔的《笛卡尔的沉思》,至于雅斯贝斯、韦伯、费罗姆,还有汤因比等人的东方思想研究,更应被看作是不着边际的翻译,因为他们对古汉语、梵文、日文等东方文字不明奇妙,全需要借助译文和译介来做翻译。那么,本来的意思已经在这种翻译中丢失太多了。或者说的直白点,丢失了语境或者更换了语境的语言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语言了,也会丧失原汁原味语言的指向意义。

禅宗讲“不立文字”、“直指人心”,或许已经超越了文字的限制,达到精神契合的境界。而对于翻译来说,人们只能在翻译的著作中寻找到原作的一鳞半爪,指望没有误译,全部掌握原著的思想似乎已经不可能了。但并不能否定翻译的意义,只是希望译者能够专业一些,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原著的精神和语境,力求准确无误,而不能只是匆匆翻译,赚钱为止。
推荐阅读:知识翻译学的创新探索
【发布时间】2022-09-05 【信息来源】管理员 【浏览点击】2177次